据《金融时报》报道,全球社交媒体巨头 Meta 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、图灵奖得主 Yann LeCun 计划离开公司,并着手创办一家 AI 初创企业。
知情人士透露,这位被誉为“深度学习先驱”的法裔美籍科学家已在内部沟通中表示,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离职。LeCun 已经开始与潜在投资者进行早期接触。
无论是 Meta 还是 LeCun 本人,目前都未对此消息发表评论。这位图灵奖得主尚未透露离职时间表,其新公司的具体方向也暂无公开信息。他在纽约大学的教授职位将保持不变。
LeCun 的离职发生在扎克伯格全力重塑 Meta 人工智能战略的关键时期。扎克伯格已逐步将重心从 LeCun 自 2013 年起领导的 Meta 基础 AI 研究实验室(FAIR)那种长期研究型工作,转向更快速地推出模型和 AI 产品。他认为 Meta 在竞争中已经落后。
不意外的离开
LeCun 的离开并不令人意外。过去几个月,他对 Meta 内部的一些变化愈发感到不满。据报道,他尤其反感公司新出台的内部研究发表规定,即研究成果在对外发布前必须经过更严格的内部审查。多名团队成员认为,这一政策限制了学术自由。
Meta 最近的组织调整也冲击了核心 AI 研究部门 FAIR。该部门经历了裁员,并在公司内部的影响力被转向由 Alexandr Wang 领导、专注产品落地的 TBD Lab。LeCun 也被要求改为向 Wang 进行汇报。
这场转向的背景,是 Meta 最近发布的 Llama 4 模型表现不佳,其落后于 Google、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最新产品。同时,Meta 推出的 AI 聊天机器人也未能在消费者中获得认可。
LeCun 一直认为扎克伯格主导战略中心的这些大模型虽然“有用”,但永远无法像人类一样进行推理和规划,这让他与上司在 AI 路线上的分歧日益明显。
在 FAIR 内部,LeCun 一直致力于研发下一代 AI 系统,希望打造出能够具备人类级智能的机器,也就是所谓的“世界模型”。这种系统尝试让 AI 通过学习视频和空间数据来理解物理世界,而不仅仅依赖语言。LeCun 曾表示,要完全实现这一架构可能还需要十年时间。
LeCun 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撇清与 Meta 最新 Llama 模型的关系,这被视为他对公司方向不满的又一信号。在 X 的一篇文章中,LeCun 表示,除了在 Llama 1 中扮演“非常间接”的角色以及推动 Llama 2 的开源发布之外,他“没有参与任何 Llama 项目”。他解释说,自 2023 年初以来,Llama 2、3 和 4 都是由 Meta 的 GenAI 团队开发的,该团队后来被 TBD Lab 取代。
此外,政治立场的分歧可能也加剧了紧张关系。LeCun 一直公开批评现任美国政府,而 Meta CEO 马克·扎克伯格则在近年逐渐让公司政策向特朗普阵营靠拢,这与 Meta 早期的立场形成了明显反差。
“如果我是他,我也会离开 Meta。”有网友称。有网友吐槽,扎克伯格现在组建的超级智能实验室跟当时创建 FAIR 一样。
据知情人士透露,LeCun 的下一个创业方向仍将聚焦于世界模型的研究与落地。
LeCun 一直不醉心于大模型研究
2013 年 12 月 9 日,当时还被称为 Facebook 的 Meta,正式宣布成立 FAIR 实验室,并公布了 LeCun 作为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入职,并领导该实验室的消息。同时,他还会继续担任纽约大学的兼职教授,在纽约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。
LeCun 在 2014 年 1 月 1 日正式加入 Facebook。当时业界普遍认为:Google 收购 DeepMind(2014 年初)、Facebook 聘请 LeCun、百度聘请 Andrew Ng,三者共同标志着“深度学习人才争夺战”的开端。
LeCun 将 FAIR 定位为一个“开放研究”机构,不仅致力于产品应用,更重视深度、基础的 AI 科学探索。在 LeCun 的领导下,FAIR 发布了多个影响甚广的开源工具和框架,例如在深度学习社区极为流行的 PyTorch 框架。
3 个月前,LeCun 还发文称,自己作为 FAIR 的首席科学家,一直专注于长期人工智能研究和构建下一个人工智能范式。“我的角色和 FAIR 的使命没有改变。”当时,OpenAI ChatGPT 的共同创造者赵晟嘉(Shengjia Zhao)加入 Meta,出任“超级智能实验室”首席科学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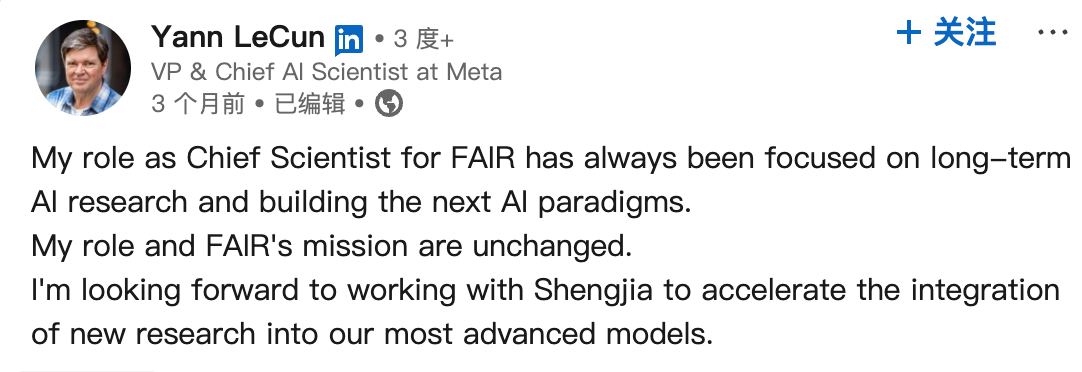
在 FAIR 时期,LeCun 所领导的团队在计算机视觉、自然语言处理、生成对抗网络(GANs)、自监督学习等方向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,这些成果既强化了 Meta 在学术界的声誉,也为公司内部产品提供技术储备。
一些网友认为,LeCun 在大模型竞赛中的表现很糟。“我无法评价他在 Meta 的研究产出,但他在大语言模型(LLM)竞赛中确实失败得很惨。既然那么多其他机构以更低成本成功创建了质量远高于 Llama 的开源模型,那么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很有意义的。”
但也有网友认为,把他在 LLM 上“失败”看得这么严重其实有点好笑。“考虑到他的职责是 8–10 年的研究周期,而且他曾公开表示,预计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技术发展会停滞,所以他实际上只能算是赢或者打平。间接地影响开源模型推动研究进展(这对首席科学家来说非常重要),也给 Meta 的其他产品带来了额外好处。”
实际上,这也是由于 LeCun 提出并推动可世界模型等研究方向,他主张探索机器理解物理世界、空间数据和多模态信息,而不仅仅停留于语言模型上。
在最近跟李飞飞、黄仁勋等人的圆桌上,LeCun 再次强调,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应用开发仍处于爆发期,这正是当下主导的技术范式,其中蕴藏着巨大潜力。但人们认为仅靠现有 LLM 范式就能实现人类级别智能的预期,他对此持怀疑态度。“要真正实现人类乃至动物所展现的智能水平,我们仍需多项根本性突破。目前甚至没有机器人能达到猫的智能水平,这说明我们仍然缺失某些关键认知模块。”
他认为,下一代人工智能的真正突破需要基础理论的革命性进展。
“在那个圈子里,LeCun 是少数几个似乎还有些正直的人之一。”也有网友指出,LeCun 的问题是,他是一个研究型人才,却在以产品为导向的组织里工作。
“他可能说得没错,大模型并不是通往 AGI 的道路,但这对 Meta 来说无关紧要,Meta 需要的是今天就能卖得出去的产品。而在创业公司里,这一点也同样无关紧要,因为他必须从风投那里筹集资金,而投资人会在两个季度后逼问他:收入增长在哪里?如果他真的相信我们需要一条通向 AGI 的新道路,那么他应该待在基础研究实验室,而不是去创办初创公司。”
失落的 Meta 员工
今年 10 月底,扎克伯格暗示公司未来的 AI 投入将继续上升,明年可能突破 1000 亿美元后,Meta 股价暴跌 12.6%,市值蒸发近 2400 亿美元。LeCun 的离职,是这家市值 1.6 万亿美元公司在这一动荡年份中又一次高层震荡。
Meta 近两年的动荡,主要来源于对大模型冲击。田渊栋在接受硅谷 101 采访时候提到,从其入职到 2022 年这段时间,大家整个工作状态都很好,团队氛围也积极。整个改变的转折点是大模型的兴起。
他表示,大模型时代,算力成为决定性因素,然而算力资源毕竟有限,而大家都想训练更大的模型,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种矛盾和竞争。如果我占用了更多算力,别人可用的资源就会变少;可如果不给足算力,又很难训练出高质量的模型。正是因为这种资源博弈,从 2023 年开始,Meta 整体的状态和氛围就不如以前那样轻松愉快了。
外行指导内行
从事 Lama 3 后训练的前 Meta AI 工程师 Gavin Wang 也在接受硅谷 101 的采访中提到,公司高层中,如 VP、高级总监这一级,很多人是基础设施背景出身,或来自传统的计算机视觉领域,甚至具备自然语言处理背景的都很少。从技术角度看,他们对 AI 原生或大语言模型缺乏深入理解,而真正懂行的,其实是下面具体执行的一些博士,他们技术功底非常扎实,但在公司内部的话语权和资源却相对有限。这在某种程度上,形成了一种“外行指导内行”的局面。
田渊栋也提到,他最大的教训就是,技术密集型的大型项目,绝不能由不懂行的人来担任核心领导或负责规划。
Gavin Wang 还指出,DeepSeek 的技术路线原本也是 Llama 团队内部讨论过的一个方向。但由于 Meta 自身的生态布局更优先多模态,推理方向并未成为重点。DeepSeek 出现后,团队内部确实重新讨论研发方向,导致优先级上出现冲突,加上时间非常紧张,大家不得不加班加点进行多种尝试,整体节奏变得异常忙碌。GenAI 团队甚至没空回复同事信息。
Meta 内部有非常大的 Deadline 压力。Meta 项目管理方式是“倒排工期”,即从发布日向前反推,规定每个时间点必须完成什么。因此,基于技术判断的“叫停”往往无法实现,延期也难,最后为了赶工期而牺牲了产品质量。
迷茫的员工
Altman 曾公开批评 Meta 以高价挖人会“制造坏文化”,并称 Meta“不擅长创新”。前 Meta 研究员 Tijmen Blankevoort 表示,他认同 Altman 的观点,并补充称 Meta 一贯难以留住从外部引进的 AI 人才。
“我见过太多天才从其他公司来,又很快离开,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文化。许多人对 GenAI 部门的厌恶几乎是出于本能的。”
Blankevoort 于去年 2 月加入 Meta,曾是 Meta LLama 模型研发团队的一员。他此前曾创立一家 AI 初创公司,2017 年被高通收购,不久前他从 Meta 离职。Blankevoort 在离职前发送了一封内部邮件,暴露了 Meta AI 部门成员饱受恐惧、混乱和职能失调的困扰。
“我还没遇到一个在 Meta GenAI 部门真正感到快乐的人。没有人觉得这里是他们想长期待下去的地方。”
“几乎没人真心相信我们的 AI 使命,对大多数人来说,甚至连‘使命是什么’都不清楚。”
Blankevoort 称许多员工感到迷茫且缺乏动力。他表示,如今规模已超过 2000 人的 AI 部门做事情没有方向,“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在这里工作,” 他补充道,“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。” Blankevoort 称,反复的内部冲突和模糊的目标正损害团队的创新能力。“这不仅仅是职能失调,而是一种转移性癌症,正在影响整个组织。”
“Meta 内部存在一种恐惧文化。” Blankevoort 将这种文化部分来源于公司的绩效评估制度与滚动裁员机制。Meta 的大规模裁员基于绩效,公司还暗示未来的绩效考核可能再次用于裁低绩效员工。“很多人不是被使命感驱动,而是被害怕被炒驱动。”
“这种态度像转移性癌症一样蔓延在公司里。” 他指出,这导致了各自为战、抢地盘、抢项目、窃取成果的内部“文化”。
他还指出,Meta 的生成式 AI 战略缺乏方向。过去两年,该部门不断叠加职责:既要做 Llama 模型,又要开发 Meta AI 助手,还要为社交平台和设备提供各种 AI 功能。相比之下,OpenAI 专注于 ChatGPT,Anthropic 专注于代码 AI,因此在营收上实现爆发式增长。
他举了 GenAI 团队与可穿戴设备团队的例子,前者隶属首席产品官 Chris Cox,后者隶属 CTO Andrew Bosworth 领导的 Reality Labs。两团队几乎没有合作,即便是在为 Ray-Ban 智能眼镜训练可运行小模型时也是如此。“我们多次建议合作,但都被无视——可能因为 GenAI 部门正因 Llama 4 的发布而陷入生存焦虑。”
“任何有清晰愿景的理性公司,都会立刻抓住这样的合作机会。但我们不是那样的公司。”Bosworth 说道。
扎克伯格还以数亿美元级别的高薪招揽新的 AI 领导者,这也引起了老员工的不满。
用 AI 救元宇宙?
近日,据外媒报道,Meta 元宇宙副总裁 Vishal Shah 向员工发出内部备忘录,要求他们使用 AI“提高 5 倍生产力”。注意,不是 5%,而是当前基线的五倍。
备忘录提到,到今年年底,80%的元宇宙部门员工必须将 AI 整合进日常工作流,明确目标是让“AI 成为一种习惯,而非新奇玩意”,覆盖编程、设计、产品管理及跨职能协作等领域。据悉,该部门已烧掉数百亿美元,却鲜有人真正使用其产品,但 Meta 不愿承认战略失败。
“这反映了科技高层在 AI 浪潮中‘魔幻思维’的复苏: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,把幻想当作计划,把绩效压力伪装成创新口号。”外媒评价称。
参考链接:
https://www.ft.com/content/c586eb77-a16e-4363-ab0b-e877898b70de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2J2TB1Ex3/?spm_id_from=333.337.search-card.all.click
https://winsomemarketing.com/ai-in-marketing/meta-says-employees-must-work-5x-faster-using-ai





